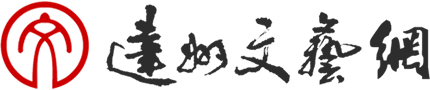本刊特别声明:未经允许,不得转载!
本刊特别声明:未经允许,不得转载!
作者简介: 罗伟章:四川宣汉人,现居成都。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,达州市创作办公室签约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饥饿百年》《不必惊讶》《磨尖掐尖》《大河之舞》,中篇小说集《我们的成长》《奸细》等。曾获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多种文学奖项。部分作品译介到英、韩等国。
这个故事发生在我遥远的家乡。秋天,一只黑色土狗来到李家坪,看样子是从山梁那边的杨家堡过来的,已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它在李家坪东院的石梯上张望,身上带着泥土,也带着成熟的谷香。李明说,一棒闷死它,和辣椒炒了下酒。坐在街檐上抽烟的李才,顺手握住横在地上的打杵,亲切地唤:黑儿,过来。它或许就叫黑儿,耳朵竖起,却没动身。李才的女人从屋里拿出半个用桐叶包的玉米粑,站到男人身前去,把手伸得老长,来呀,她说,给你吃你还不来吗?它大概已流浪了好几天,路上没找到什么吃的,肚子瘪得风一吹就晃动。它朝李才的女人叫了两声,这两声连在一起,听上去怪怪的,像变了腔在叫“妈妈”。这是一条小狗,不过尺来长,正是叫妈妈的年龄。一个院坝的人都笑,说李才啥时候养下这么个私生子?李才的女人红着脸骂:你们这些砍脑壳的,狗肉炒熟了都别想拈一筷子!说罢,她把玉米粑放在地上,用脚尖点,黑儿,乖,过来吃。
小狗摇着尾巴,迈开了步子,只是走得相当慢,细细的腿颤抖着。
它离玉米粑还有一米左右,李才偷偷站起身;那根被他握住的打杵,也跟着他站起来。
那一刻,院坝里很静。
小狗黑儿站住了。它只看见李才的女人,没看见李才,更没看见李才手里的凶器。它站下来,只是想再叫一声“妈妈”。这一声叫得更像,也更缠绵。李才的女人红了眼圈,把玉米粑往前踢了一下。男人在背后骂她,说要是没打着,让狗跑掉了,看老子怎么收拾你!李才的女人并不怕他,笑着回骂过去:跑掉了就跑掉了,你把我卵咬一口!黑儿听不懂他们的话,又朝玉米粑靠近,当它把头低下去,抽动鼻尖闻气味时,李才的女人闪开身,悄声对男人说,赶快下手!
李才将打杵高高举起。
这时候的小狗黑儿,就像古装戏里的死囚犯,刽子手正要动刑,突然听到一声高呼:刀下留人!
喊这一声的叫李贵东。当然没说刀下留人,而是说:莫打,我养它。
李才的打杵还举着,扭过头问:贵东叔,你真要养吗?
李贵东说,我养,还是个奶娃娃就遭闷棒,可怜。
既然这样,李才就把打杵放下了。黑儿把那半个玉米粑吃得干干净净,连外面包的那层桐叶也没剩下。之后,李贵东把它唤进了屋。
要追述这层院落的历史,就太久远了。整个李家坪,包括杨家堡,都是“湖广填川”时期的产物。李家坪共有三层院落,除东院,另两层院落都有较为频繁的人员流动,东院却是稳定的,多少年来,都是这四家人居住,出去的,是嫁了的姑娘,进来的,是娶进的媳妇,至于那些出门打工的年轻人,家都还在这里,逢年过节的也要回来(只有李贵东的小儿子在成都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,回来得相对少一些),并不影响家庭的核心。老人死去了,小孩成长起来,血脉代代延续。
眼下,年龄最大的就是李贵东,已过八十岁。
李贵东的妻子三十前就去世了,几年前他自己也成了残疾:那天他在院坝外的青石坎上踩虚了脚,左胯骨摔断,皮肉伤好了,骨头却没长拢,走路搭不上力,只能拄拐杖。他的小儿子有一回去登华山,见有卖拐杖的,就给父亲买了一根。是根曲曲弯弯的龙头拐杖,杖身漆成彩色。李贵东用了一段时间,觉得色彩艳丽得晃眼,使他看不清前面的路,就丢到墙角去,自己做了一根。这根拐杖用材质细密的梨木做成,实沉,稳重,皮面光溜,黑夜里也能感觉出它的亮度;它在山林里长了许多年,不知吸进了多少阳光。李贵东拄着这根拐杖,在院坝里出入,也在田地里出入。他有两个儿子,三个女儿,大儿子李建华也在东院,但他不愿跟儿子住一起,当然更不愿去跟女儿住。人老了,害怕孤独,更害怕寄人篱下。即便被儿女供养,李贵东同样能尝到寄人篱下的凛冽气息。他幼年丧父失母,使这气息从头至尾地贯穿着。正因此,他才怜悯小狗黑儿,收养它后,把它当人一样看待。别人喂狗,都是饭后赏一瓢残羹剩汁,有的人家甚至不喂,让它去外面找屎吃;李贵东喂黑儿,都是先把饭菜搭配了,倒进门边一个缺了角的陶钵里,自己再坐下来吃。李才跟他开玩笑,说贵东叔,你干脆把黑儿叫李建华算了。那时候李建华也在场,给了李才一个脑瓜嘣儿,李才又返过来给了李建华一个脑瓜嘣儿;虽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人,笑闹得还像孩子。
东院这四家人——李贵东、李建华、李才,李明,相处得是相当和睦的;东院历来就比另两层院落能捏到一块儿去,之所以稳定,就因为这个缘故。
谁知道黑儿来了不过二十天,东院就散了,不再和睦了。
事情从李明家的鸡开始。
李明家孵出了一窝小鸡,共二十四只,那二十四只米黄色的鸡娃,跟随母亲在院坝里觅食。院坝由石板铺成,晒粮食的时候,一些麦粒和谷物,从接缝处漏下去,鸡们把那些粮食掏出来,和泥土吃掉。一个院坝都是鸡娃喳喳的欢叫。小狗黑儿却很孤单。东院唯它一条狗,另两层院落虽各有一条狗,却都是凶恶的大公狗,各自划分了领地,黑儿也是公狗,天生懂得狗道上的规矩,知道要想不丢小命,就不能越界。李贵东下地干活的时候,它跟前跟后,仿佛它知道主人的腿不好,生怕他摔倒。可是主人回到家里,它就无所事事了,像一个孤单的少年,坐在街檐上,看着远处飞翔的云朵,神情忧郁。时不时的,它把目光收回来,鸡们到了哪里,它就看向哪里。或许,那时候它想起了自己的母亲,想起了自己走失之前的美好时光。它希望融入这个新环境,没有狗,就跟鸡打成一片。于是它慢吞吞地向鸡靠近。李明家的那只笋壳母鸡,似乎有些瞧不起它,明知它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,但就是看不惯它那张尖嘴猴腮的脸,见它过来就扇开翅膀追。母鸡一追,黑儿就跑,母鸡不追了,它再停下来。渐渐的,它发现这种游戏很好玩,故意去惹母鸡,让它追赶自己。
这游戏没玩多久,就被人发觉了。那天它偷偷绕到母鸡背后,兴奋地挠了母鸡一爪,母鸡十分气恼,咯咯乱鸣,把它在院坝里追了两大圈。母鸡的鸣叫引出了李明。
李明在家里煮猪食,手里拿着火杈,见黑儿从他脚边跑过,他一火杈打在黑儿身上。
黑儿跑开了,直跑到李贵东的街檐上,才敢痛苦地叫唤。
从那以后,它不敢靠近李明家的鸡群了。
这样的日子是难熬的,它远远地坐在一旁,看李明家的小鸡怎样长大,怎样玩耍。当母鸡把翅膀铺开,小鸡挨挨挤挤地钻进翅膀底下后,它站起来,离开了。
但也有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。这时候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院坝里游走,在母鸡能够容忍的地界,它躺下来;为表明态度,它脊背着地,肚皮朝天,后腿绷直,前爪弯曲。进入秋季,李家坪总是漫无边际地晴朗着,天空深蓝,蓝得发愁。蓝天之下的小狗黑儿,被和暖的阳光融化,被柔软的风融化,也被鸡们彼此的呼唤融化。它觉得这样很幸福。
如果维持现状,黑儿很可能一直幸福到老死,可问题是,李明家的鸡丢了。
那天早上起来,李明坐在青石坎上发呆,笋壳母鸡领着它的孩子经过他面前时,他觉得小鸡好像少了些,便开始清点,点第一遍,是二十二只,点第二遍,是十九只,点第三遍,是二十一只。他骂了声娘,站起身点第四遍,且用手把点过的鸡拦开,结果跟第一遍点出的数目一样,二十二只,没错!他朝屋里的女人喊:桂秀,我们的鸡娃少了两只呢!桂秀脸上糊着锅灰,惊惊乍乍地跑出来,跟李明一样,把鸡连点了几遍,确定之后,返回屋子的鸡埘里去找。鸡埘里只有鸡屎,没有鸡。这时候李明也跟了进来,说肯定是黑儿把鸡咬死了,那天我看到母鸡在追它,我还给了它一棒。桂秀说,咬死了总会留下鸡毛吧,快看看哪里有鸡毛。两人房前屋后地寻鸡毛,把整个早晨搭进去,只寻到零星的几根,那明显是自然掉落的,与杀戮无关。两人又去茅坑里搅,搅得一个院子弥漫着臭气,依然没有小鸡的影儿。两口子累得大汗淋漓,站下来商量,商量的结果,还是觉得黑儿是最大的嫌犯,毕竟,李明亲眼看见母鸡追它,如果它不咬小鸡,母鸡又没发疯,追它干嘛?
吃过午饭,李明进了李贵东的家门。那时候李贵东正热冷饭。他每天早上把一天的饭煮好,中午和晚上热一热就是,黑儿来之前,许多时候他中午也在坡地里忙活,一天只吃两顿,黑儿还是个孩子,吃两顿受不住饿,把冷饭给它带到坡地里去吧,又怕它吃了坏肚子,于是李贵东也就沾了黑儿的光,一天吃三顿。李明进屋在条凳上坐了,李贵东就去给他拿叶子烟,李明说,贵东叔,你别去麻烦,我问你个事。李贵东回转身。李明说,我家的鸡娃少了两只,可能是黑儿作的孽。李贵东一听,脸就黑下去了,我黑儿顿顿都吃得饱饱的,它咬你家的鸡干啥?李明说它不一定吃。不吃它就更不会咬,它又不是狼。李明笑起来,它当然不是狼,要是狼,我那一窝鸡娃都被它吃了。
李明这意思,分明还是怪的黑儿,李贵东很窝火。那天李明用火杈打黑儿,他是知道的,他那时候心里就窝着火。他说,前两天黑儿跟我去地里,看到一只受伤的喜鹊,它也没咬它,只是跳前跳后地逗喜鹊玩儿。李明哂笑了一声,显然是不相信。
这时候,黑儿汪汪地叫了两声。它躲在傍里墙的八仙桌底下。它本来摊头摊脑地睡在靠门的火堂围石上的,见李明进来,迅速跑到八仙桌下躲起来了。自从那天挨了打,它就怕李明。李明和主人的对话,它尖着耳朵在听,它汪汪叫唤,像是在为自己申辩。可是人听不懂它的话。
李明说,贵东叔,没啥,少两只就少两只,现在的鸡娃也值不了几个钱。说罢他走了。
那顿饭,李贵东把黑儿喂得更饱,倒不是担心它真的去用别人家的鸡填肚子,而是觉得它受了委屈。
李明家的鸡娃在接二连三地减少,三天之内,又少了七只。
跟前面一样,没有任何线索。
李明的女人桂秀找上门来,桂秀说,贵东叔,你能肯定黑儿没咬我家的鸡吗?
没咬!
桂秀说,贵东叔,那我就骂了。
你随便骂!
乡里人丢了东西,不是去镇上找警察,而是骂。多少年都是这样的。桂秀站到院坝边,骂了一个下午,第二天一早又跑到屋后十余丈高的渠堰上,骂了一个上午,骂得嗓子咳出血丝,完全出不来声音为止。这样的长篇大论,归结起来,无非是祖宗八代的下半身。至于谁的祖宗八代,骂的人自己清楚。自己家丢了东西,或者遭到莫名的侵犯,心里都有一个假想的盗贼或敌人。
李贵东听了一个下午,又听了一个上午,左右觉得不是滋味儿。桂秀虽是泛泛地骂,可总有那么一言半语,泄漏她的所指。从“心比狗毛还黑”这样的话,李贵东听出来了,桂秀骂的就是他,桂秀认为黑儿去咬她家的鸡,是李贵东指使的。李贵东心里难受,就去找儿子李建华。他说建华,你听出来没有,桂秀像在骂我。李建华早就听出来了,很想出去跟桂秀接腔,可一旦接腔,势必吵起来,东院已经多年没吵过架了,四家人都为此自豪,每逢另两层院落的人吵架,他们都觉得,为球那么大点儿事,就吵得脸红脖子粗,简直是胀饱了饭没处消化。李建华不想去开这个头,丢这个脸。再说人家最多只是含沙射影,又没指名道姓地骂李贵东,你出去接腔,不恰好证明心虚么?虽没接腔,李建华的怨是蓄起来的,正找不到出处发泄,父亲进来问他了。
他说,你也知道是在骂你呀?该背时!
李贵东站在儿子的火房中央,可怜兮兮地舔着嘴唇。
因为左腿搭不上力,尽管有梨木拐杖的支撑,他的站姿依然是倾斜的。
李建华说,那天李才要把它打了,你偏偏多事,要养它,这下好了,养出事来了!
李贵东说,出天大的事,反正不是黑儿的错。
人家认定了就是它的错!
她又不是天王老子,她咋说就咋说?
未必你是天王老子?你说不是黑儿,你拿得不是它的证据吗?——要是我,早就一棒把它敲死!
这时候,小狗黑儿静静地立在主人身旁。
在儿子那里没获得同情,李贵东黯然地走了。
黑儿紧紧地跟在主人身后,主人快,它也快,主人慢,它也慢。
回到家,李贵东想用根绳子把黑儿拴起来。可李家坪人养狗,还没有把狗拴起来的先例;再说李贵东已经离不开黑儿了,他去空旷沉寂的坡地里干活,要是没有黑儿的陪伴,真不知道该怎么熬。他拄着拐杖,带着农具,哪里腾得出手再牵一条狗呢?
他没拴黑儿,只是告诫它:你不要到他们那边去!
黑儿像是听懂了“他们”指的是谁,在院坝里玩耍时,不再去李明的房门前。
可李明家的鸡娃继续少下去,少到只剩九只的时候,桂秀背到镇上去卖掉了。一路上,免不了又是一番好骂。买走她鸡娃的,正好是杨家堡一个妇人,她对那妇人说,我的鸡娃本来是二十四只,现在只剩九只了,那十五只,都被狗咬死了。妇人说:可惜!桂秀说,那条狗还是从你们杨家堡过来的呢,被我们院子一个死老头收养了,他收养它就是为了咬死我的鸡!究竟是你们哪家的,赶快来收回去,免得那老不死的再唆使它害人!妇人说,那狗长得啥样?桂秀把黑儿描述了一番,妇人听后,摇着头说,没听说杨家堡有这么一条狗……
李贵东父子和李明夫妇都各自怀着怨恨,但心照不宣,劈头一碰的时候,招呼是要打的,只是脸上绷得很紧,招呼和应答都很短促。
紧接着,李才家的兔子又不见了!
李才把兔子养在虚楼下面的空牛圈里,是十二只断奶不久的小白兔,长得好好的,桂秀去把鸡娃卖掉后,却突然不见了一只。李才和他女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黑儿,但没有声张,两口子不分白天黑夜,轮流守候了两天,结果黑儿根本没往他们虚楼底下去。可不是它,又是谁呢?李家坪没有猫——以前有过几只,三个月前都不知所踪;这山上也没有狼,更没有虎,听说祖先们刚从湖北迁徙过来的时候,狼是这架山上的主宰,还有零星的豹子,当山上来了人,人就成为主宰,狼和豹子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斩尽杀绝;连蛇也很难看到了,十年前,山里人就开始捉蛇,用蛇皮口袋装了,卖到镇上和县城的酒楼里,现在你到最潮湿阴森的林子去,也不必担心会踩到蛇。唯一的杀手,就只剩下狗了。而那两层院落的两条大狗,是从不到东院来的,如此推断,凶手只有一个:黑儿。
没抓到证据,李才和他女人不想贸然说出去,免得彼此交恶。
可就是那么疏忽一下,他家的白兔又少了一只。
这下不能不说了。李才很讲策略,不给李贵东说,给李建华说。他跟李建华只相差半岁,从小一块儿长大,一块儿上学,一块儿做讨人嫌的烂事,关系非李明可比。
李建华听了,说,把它龟儿子叫过来。
李才以为李建华要打黑儿,急忙阻拦:要不得,贵东叔听见了,会发气的。
但李建华不是要打它,而是把它唤到了李才的牛圈外。牛圈的木栏有半人多高,前面的门已有两年没打开过,因为李才家有两年没养牛了,兔子关进来后,放草都是从上面扔进圈里。
爬上去!李建华对黑儿说。
小狗黑儿被夹在李建华和李才夫妇之间,望望这个,又望望那个,不知所措。
叫你爬上去!李建华大喝一声。
黑儿呜呜地叫,恐惧的阴云,在它无辜的眼里飘来荡去。
别说它听不懂小主人的话,就是听懂了,牛栏那么高,中间又无缝隙,它怎么能爬得上去呢?
李建华的意思,就是要让李才看看。为让李才看得更清楚,他把黑儿抱起来,放到牛栏顶端。黑儿四条细腿抓住木板,身体摇晃不定,想跳下来,又不敢,只是哼哼地哀鸣着。
李贵东在叫黑儿了:黑儿呢,吃饭了。平时这么一叫,黑儿必然飞蹿到门槛底下,前爪往门槛上一搭,再像孩子那样把身体耸上去,可今天叫了好几声,也没见它的影子。李贵东走出屋外,隐隐约约地听到它的哀鸣声,就朝声音寻过来。李才一把抱住黑儿,将它放到地上。黑儿从李建华的两腿间钻过去,跑了。李才笑着对李建华说,看来不是黑儿。话音刚落,李贵东到了李才的虚楼底下。他见黑儿惊惶失措地从这边跑出去,想来看个究竟。
李才见了李贵东,说贵东叔,黑儿刚才差点儿滚进了茅坑。
李贵东说:……哦。
当天,李才用一个大篾篓子把兔子罩住了,四只角上,还用石头压住。
他家的兔子没再丢,但他女人还对那只丢了的兔子耿耿于怀,有一天她看见黑儿,对李才说,那狗东西,比人还精灵,那天它躺在牛栏上那副害怕的样子,依我看就是装的。
这话被李贵东听见了。黑儿躺在牛栏上?这是怎么回事?那天李才说它差点儿滚了茅坑,李贵东就疑心。李才家的茅坑没挖在牛圈旁边。因为儿子当时在场,李贵东就去问李建华。
李建华说,他家丢了一只兔子,怀疑是黑儿干的。李贵东说,放屁,牛栏那么高,黑儿干得了吗?李建华恨了父亲一眼,你小声点行不?我也是这么给他们说的,还把黑儿抱上牛栏,让它自己下来,它根本就不敢下来,更别说翻进去,叼着兔子再翻出来。他们虽然口头上说不可能是黑儿干的,心里还是那么在想。李贵东气得胡子一翘一翘的。李建华说,人家只是怀疑,又没像桂秀那样咒你祖宗,你该知足了,谁叫你养那么个东西呢!
这时候,小狗黑儿跟往常一样,静静地立在主人身旁。
李贵东心里憋着一口气,终于憋出病来。几天后病好了,那口气却没有消。
秋风起,更深人静的时候,黑儿睡在柴窝里。柴窝就在火堂边,李贵东睡之前,特意在火堂里埋了一些炭火,黑儿并不冷,但它就是睡不着。主人病这几天,都是小主人给他送饭。小主人可没准备它的饭,主人不好找儿子要,都是等儿子离去后,再拄着拐杖,艰难地支撑下床,把饭菜分出一半到它的陶钵里。主人没吃饱,黑儿也没吃饱。它有些饿,便调整了睡觉的姿势,肚子顶住柴禾,这样它不再那么饿了,可依然睡不着。从东院人看它的眼神、对它的态度,从主人的病,它知道自己犯了错误,错在哪里,却一无所知。为此它忧伤起来。
清冷的月光,从格子木窗照入户内,使夜晚静得深不可测。到后半夜,黑儿听到一丝神秘的声响。它转动耳朵,捕捉那声音。这显然不是风声,因为声音里带着热度,藏着某种目的。
它警觉地把头抬起,发现火搭钩上潜伏着一只猫!
正是一只猫。但不是一只普通的猫。这只猫曾被坡脚一户人家养着——这面山差不多等距离地分成三个聚居的群落,由下而上,分别是河底、坡脚、李家坪——养了一年多,就将其赶出了家门。它硕壮得不像家猫,而像山猫,它的职责是咬老鼠,可它觉得咬老鼠的勾当太低级,理直气壮地放弃了这份职责,专咬被山里人称为小牲口的鸡鸭鹅兔,它动作灵敏,脚步轻盈,从不在现场留下痕迹,也不知把猎物拖到哪个隐秘的山洞里吃掉了。它的破坏面,波及坡脚十多户人家,成为了人的公敌。养过它的人说,你们见到那畜生就打,打死算数!围剿那只杂毛大猫,在坡脚几乎形成一场运动。它受伤无数,却没被打死,因为很难抓住它,都只能远距离地以石头棍棒相击。终于有一回,它上楼梯的时候,被人逮住了后腿,那人风快地舞动数圈,再奋力一扬,阳光底下,一团斑斓越过院坝,越过竹丛,在干硬的、布满牛蹄印的路面上炸响。谁都以为它死定了,哪知它只是惨叫一声,翻身就跑。不过从这以后,它知道坡脚再不能待,便穿林越壁,一路上行,到了李家坪。它到李家坪做的第一桩事,是杀死同类。这是一件相当简单的工作,猫们见了它,无不站定不动,尿液直流,它只需慢条斯理地走过去,在它们柔软的脖颈上留下牙印,问题就解决了。它早就懂得,自己能斗过很多种动物,就是斗不过人,因此昼伏夜出,不在人的视野里出现,杀伐尽量干净利索,之后再带到远远的地方藏匿或享用——对那几猫和李明家的鸡、李才家的兔,它就是这样做的。
吃掉了李才家一只兔子,它本能地感觉出东院的危险,于是去另两层院落寻视了几天。遗憾的是,收获相当微薄,它饿得不行,又返回东院。今夜里,它从李贵东的格子木窗挤进来,通过房梁把自己倒挂在火搭钩上。那里,挂着一块腊排骨。
黑儿看见它的第一眼,就知道自己不是它的对手。猫的身体比它还长,眼睛比月光还冷。黑儿静静地扭动着身体,把自己藏在柴窝深处,只露出脑袋。其实猫早就注意到它了,只是没把它放在眼里。火搭钩是生铁扭成的,长年烟熏火燎,积满了烟油,每年杀了年猪,都把漤了盐的肉挂在上面,又积下许多猪油,因而很滑,猫的尾巴和后腿在火搭钩上缠搅着,前爪伸直,想把排骨抱起来,咬断上面的棕绳。这些事情,它完成得那么从容镇定,黑儿被深深地刺痛了。它既屈辱又愤怒,鼓足勇气,狂吠起来:汪汪汪——汪——汪汪汪汪汪……
猫瞪着它。猫的眼睛像两粒射向它的银色子弹。猫在考虑是不是先跳下来,抓瞎黑儿的双眼再来完成它的事业。可里屋传出人的声音。那个苍老的声音说:背时东西,吵死呀?
接着响起亮灯的声音,棍棒的声音,走路的声音。
猫纵身一跃,上了窗户。
接连好几天,黑儿都在深更半夜狂吠。因为猫一直惦记着李贵东家的那块腊排骨。
黑儿十分警觉,一见它在窗口出现,立即吠叫。
李贵东很奇怪,未必有贼?李家坪已经十多年没贼了,以前过穷日子,家家户户都养狗,那是为了防贼,现在狗养得少,是因为都吃得上饭,犯不着冒着巨大风险去钻别人的屋子。但前两三夜黑儿吠叫的时候,李贵东都起来看看。看的结果是除了被风吹得飘起来的月光,啥也没有。之后他就不起来了,当黑儿再一次吠叫,他只躺在床上安抚,说黑儿你放心,有我在,没人敢把你咋样,别叫了,你再这么叫,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就会把你当成疯狗了。听话,好好睡啊。
虽然人没起床,猫毕竟有了顾虑,始终没能把李贵东那块腊排骨偷走。
这让它十分恼怒,决定惩罚黑儿。
黑儿是被人保护的,它却是人的敌人,人的敌人要惩罚被人保护的对象,谈何容易。对此猫认识得很清楚,不轻意下手,只待时机。这其间,它在林子里扑到了一只粗心大意的翠鸟,之后又犁开夜色潜行到东院,跳上李贵东的格子木窗。它好像觉得,作为一代猫王,竟弄不到一块腊排骨,是很丢脸的事。沉寂了两天的黑儿,又叫起来。
东院的格局是这样的:李建华单门独户地住在临河的一面,其余三家傍山,李贵东居中,李才和李明分居左右。李才和李贵东之间,间着一条巷道,李明则跟他仅一壁之隔,且是板壁,黑儿的吠叫,还有李贵东说的那些话,李明夫妇听得分明。别说这么大的响动,就是隔壁翻个身,放个屁,也能听清。有一天,黑儿的叫声刚停,桂秀说,硬是他妈条疯狗!这话显然是说给李贵东听的,否则不会等黑儿安静下来才说。李贵东也知道,桂秀骂的不是黑儿,而是他。他再也睡不着了,心想自己从小孤苦,而今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,小儿子还做了大学教师,却照样被人像狗一样骂……
那只猫在村外的林子里徘徊,想再抓鸟,可这工作比进院抓鸡还难。别以为这么一架大山就有很多鸟,其实这山上的鸟少得可怜,麻雀一只也没有,几十年前的那场灭雀战,这山里人功绩卓著,受到过省报表彰,从那以后,麻雀宁愿飞到城市的饭馆前拾人牙慧,也不回这块伤心之地吃丰盛的野果;别的鸟类,被越用越毒的农药杀得差不多了。猫再次进村。这次它是白天来的,当它站在李明家的瓦屋顶上,看到了躺在院坝里的黑儿,积存的怒火,使它无声地咧开嘴,把尾巴竖成旗杆。院坝里无人,正是教训黑儿的好时机。它跳到房梁上,沿柱头往下滑翔。
小狗黑儿全无察觉,直到被狠狠地抓了一爪,猫迅捷地爬上柱头之后,第一声惨叫才发出来。
等李贵东拄着拐杖出门,看到的只是头上流血的狗。
他不知道是猫的干的,以为是人干的,把拐杖在石地上戳得乱响,破口大骂。
猫有了一次白天出没的成功经验,胆子大多了。这天傍晚时分,它到了李建华当门的黄桷树上。李建华家一公一母两只大鸡,在黄桷树下的草丛里找虫子,找得很不专心,公鸡老是去骚扰母鸡,当公鸡终于得逞,便走到一边去,母鸡则显出疲惫的样子,身体伏下去歇息。猫就在这时候开始了行动。它在浓密的枝叶间如履平地,目光把母鸡钉住。它没注意到小狗黑儿来到了黄桷树上方那个废弃的石碾旁边。它飞纵而下,在母鸡身上撕扯的时候,黑儿的叫声也起来了;黑儿头上的伤还没好,疼痛还在折磨它,它不敢与猫正面冲突,边吠边朝院坝飞跑,直跑回主人的家里。
李建华和他女人那时候正吃饭,听到鸡鸣狗吠,李明把碗一放,跑到虚楼上去看。
猫早已隐入黄桷树的密林,他的那只母鸡,毛掉了一地,脖子搭下去,看来已经死了。他从前门出来,从石梯冲到黄桷树跟前,提着死鸡,回了院坝。
狗日的,他大声说,黑儿硬不是个好东西,它把我的生蛋母鸡咬死了!
院坝里所有人都听见了,除李贵东,都走出屋外。
李才说,我说我的兔子是遭它搞掉的,你还不信!
李明和他女人桂秀,发出响亮的冷笑声。
这时李贵东拄着拐杖正在扫地,小狗黑儿围在他的腿边转悠。猫带给它的恐惧还没消除,它需要主人的保护。然而,听到儿子和李才的话,听到李明夫妇的冷笑声,李贵东停下了手里的活,举起拐杖,一棒敲在了黑儿的头上。
黑儿不知道怎么回事,前半身伏下去,凄哀地望着主人,发出抽泣似的鸣叫。
李贵东又是几拐杖打下去,一棒比一棒狠。
黑儿不叫了,嘴角渗出血丝,四条细细的腿抽搐了几下。
李贵东也在抽搐,可他把黑儿提起来,手一扬扔到院坝里,一蹶一拐地冲出去,照着死狗又是一阵猛捶。
院坝里很安静。
……
死狗在院坝里晾了一个下午。
天快黑下来的时候,李才进了李明的家门。不一会儿,李才跟李明一道,进了李建华的家门。李才先开口,他说建华,为黑儿的事,惹得贵东叔生气。李建华也正生父亲的气,李明家的鸡、李才家的兔,他没亲眼看见是黑儿咬的,他自己家的鸡,却是亲眼看见——他把推测当成了亲见——而父亲非但不给个说法,还把已经打死的狗扔到院坝里继续打,是要做给谁看?他说,生他的气,人老了,变糊涂了!李明说,贵东叔没糊涂,他只是没想过来,为一只狗,犯得着吗?李才给两人递过一支烟,说,建华,我跟李明的意思,黑儿反正已经死了,扔了可惜,还是打扫出来做道菜,我们几家人打平伙,你出那只鸡,李明出个腊蹄膀,都拿到我家里去做。当初黑儿来的时候,是我准备闷死它请大家的,现在,虽然在我家做饭,就算你们请我吧。几人笑起来,算是达成了协议。
现在的问题,是要把李贵东的工作做通。几人一番商定之后,一起进了李贵东的家。
这次李明的话说得多一些,特别骂了自己老婆,怪她不该爹长妈短地骂人,说有什么地方冲撞了贵东叔,请贵东叔谅解;说贵东叔是这院里的长者,我们都很敬重,贵东叔大人大量,不跟婆娘一般见识。这么说了半个时辰,李贵东含泪答应了。不答应又能怎样呢,小狗黑儿已经死了。
而且是他亲手打死的。
那天夜里,几家人喝了很多酒,说了很多话,显得格外亲热。
李家坪东院,又和睦如初。
这时候,秋天还没过完。
顺便说一句的是,李贵东是我的父亲。几个月后,我从成都回家过年,听说了小狗黑儿的事(也听说了那只猫的事。他们终于发现了那只猫,跟坡脚一样,没能把猫打死,只是把它吓出了李家坪,而今,不知它又到哪里流浪去了),我独自走出家门,踏着积雪上了渠堰,望着苍茫的群山,心里念叨着一句话:黑儿,我们来世做兄弟……
雪还在下。漫山遍野的雪。